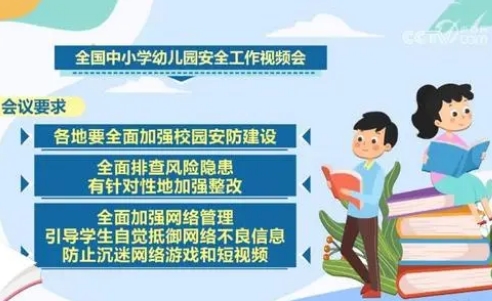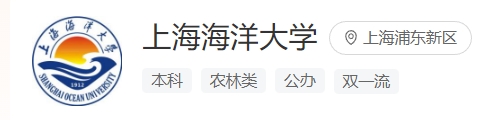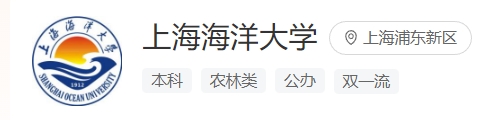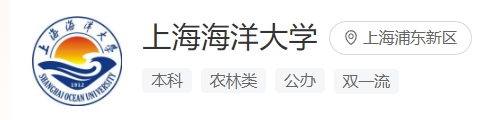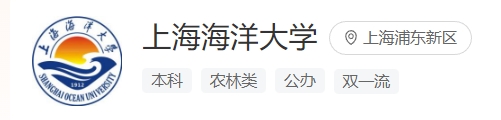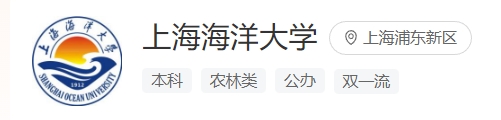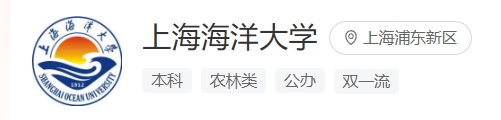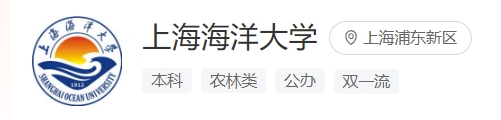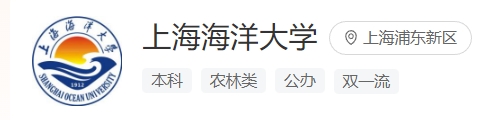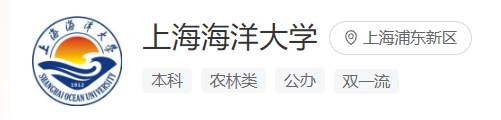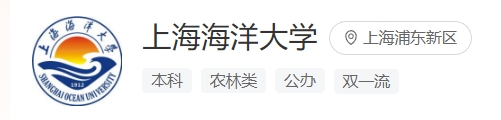3月3日,列席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開幕式的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對媒體表示,高考改革方案“很快會出來”,甚至“用不了十個月。”此言一出,社會嘩然。
如何兼顧北京家長和孩子利益的同時,不損害非京籍納稅人及其孩子的合法權益成為當前焦點問題。有家長清醒地認識到,異地高考之爭,“不是一個群體和另一個群體的利益競爭,也不是一場零和游戲。從長遠來看,大家都是受害者。”
高考地的兩難選擇
“我兒子已經上高二了,多半是趕不上了。”看到新聞,申益并沒有松一口氣。
2000年,作為某IT高新技術企業的引進人才,申益成為第一批北京工作居住證持有者在北京工作。“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孩子就在北京讀書,因為有北京綠卡,在讀中小學時享受市民待遇。”
“孩子小的時候,總想著離高考還早,以后政策就變了,沒曾想一晃10多年過去了,還沒任何松動。” 申益無奈地嘟囔。
申益目前最現實的難題是,如果政策不變,孩子明年就得回老家高考,而根據當地規定,有戶籍但沒有學籍的孩子只能以社會考生身份報名,不得報考提前錄取院校、軍校,“可兒子一心想進軍校。”
與申益有著相同困擾的家長并不在少數。根據我國目前的高招制度,考生只能在戶籍所在地參加高考。以北京為例,據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數據,截至2011年秋季開學,義務教育階段有47.8萬多隨遷子女。在現有政策下,這些孩子只能以借考形式參加中考,不能報考北京市高中,不得在京參加高考。
“但回老家也不行啊。”山東人張猷說,拋開家長的難處不說,孩子從生活上到學習上都很難適應,“各地高中教育方式不一樣,甚至考試科目都有差別。而且交流都成問題,尤其是江浙一帶,一口京片子的孩子回家連方言都聽不懂。”
2006年,張猷被單位派到北京接手分公司的管理,“當時把老家的房子都賣了。” 姐姐的前車之鑒讓張猷打定了主意,“絕不把孩子送回去。”
“我姐在北京呆了20多年,沒有北京戶口,兒子初中時轉回山東。但沒有家長管,老師又管不過來,加上這個階段的孩子正處于青春期,叛逆、自制力不強,養成了很多壞毛病。無奈之下,孩子上高三時,我姐只好再回山東咬咬牙又買了套房,專門陪兒子讀書。”類似的故事,在隨遷子女家長的QQ群里還有很多。
“為什么孩子們從上幼兒園開始就在一起,長大了反而被劃上了另類的印記呢?”2005年就帶著5歲的兒子來北京的武濤說,從上幼兒園開始,同班家長就建了一個QQ群,她是群主,“大家在群里一起討論報哪個興趣班,周末去哪玩,關系很融洽,他們不知道我沒有北京戶口,我們生活在一起,感覺都一樣。”
但武濤發現,現在上六年級的兒子早已明白了外地學生和本地學生的區別,比如外地孩子不能享受“一老一小”醫保。“學校每年發醫療保險表,他會跟我說,媽媽,那個表我們不用填。”
“最近看電視,兒子看到留守兒童這個詞,就問我是什么意思。為了方便理解,我說,以前在老家,對爸爸而言,你就是留守兒童。沒想到,兒子低頭想了想說,哦,那我很快又要成留守兒童了。”武濤聽了很心疼,“戶口就像卡在我們每個人頭上的緊箍咒,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緊。我們以為孩子小不懂,其實他什么都明白。”
與武濤一樣,申益和張猷都曾遭遇類似的情況,因為沒有北京戶口,有體育特長或音樂特長的孩子沒法代表學校比賽,評三好生、優干也往往有諸多阻礙。
張猷有一次還因此去學校理論了一番,“孩子是學校的打擊樂首席,有次參加大型演出,表演前沒幾天突然把我的孩子撤下了,換上了一個北京孩子。我氣不過,去學校找老師。學校最終出了個折中方案,兩個人的表演變成了3個人。”
張猷覺得,表演是小事,但孩子應該有被公平對待的權利,“我不想讓他覺得,自己被劃成了另一類人。”
盡管面臨兩難抉擇,但多數城市新移民不會再返回原籍,因為相當一部分新移民的事業、家庭、不動產、交際圈均已扎根在遷入的城市,返回原籍面臨著巨大的代價,有些孩子甚至因此“被留學”。
京籍家長的擔憂
一邊是隨遷子女家長群體越來越高的放開異地高考的呼聲;另一邊,則是在北京、上海這些熱點地區本地戶籍家長的擔憂與反對。
據報道,此次兩會上,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表示,解決異地高考的問題,“既要想到解決隨遷子女的考試問題,又不能影響北京、上海當地考生的權益。”他認為,解決異地高考的問題之所以難,就難在“既有要解決的問題,又有不能碰的問題。”
杜玉波也坦承,異地高考放開,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阻力主要來自于當地居民,所以各地要把這些矛盾處理好,在準入門檻上仔細測算好才能確定。
3月9日、3月13日,在“e度教育社區”論壇里,有網友陸續發表了“北京家長針對‘異地高考’等問題的幾點意見”,以及《北京市民致教育部的公開信》,引發網友關注和跟帖。
在公開信和意見中,京籍家長也表達了自己的擔心:放開流動人口子女參加本地高考,會對本地學生造成沖擊;因洼地效應而產生的高考移民(微博),進一步加劇城市的承載壓力。并提出在小學、初中、高中、高考階段對外來人口子女實行不同的限制方案。
北京市民田芳說,雖然她的孩子還在幼兒園,但她已切身感受到了幼兒園入園難、小學入學難,更不用說從周圍同事孩子小升初中感受到的驚恐和艱辛。她覺得,外來人口的快速增加已經給京籍家長帶來了壓力,“我所在的小區就有隨遷子女家長,他們基本都生了二胎,這些人要么在公司打工,要么做小生意,國家對他們的超生行為無法監管。”
田芳說,“這不單是一個高考的問題,必須看到其背后一系列引發的問題。”
在論壇上,網友墨寶說,“開放高考涉及到的地方財政、城市管理、社會保障、醫療交通乃至計劃生育方面,這些問題都考慮了嗎?你們不覺得北京已經不堪重負了嗎?”
田芳擔心,一旦放開異地高考,北京會涌入大量外來生源,“較高的升學率一直是北京的優勢,一旦放開,必將吸引更多人落腳北京,戶籍制度也將被徹底架空,是否會形成新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在兩會期間,不少代表也提出了開放異地高考所面臨的現實困難,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地,高考競爭相對不激烈,人口流入多,是異地高考矛盾最復雜最尖銳的地區。
“這不是一個群體和另一個群體的利益競爭,也不是一場零和游戲。從長遠來看,大家都是受害者。”一開始,看到網上京籍家長言辭激烈的反對意見,武濤會很生氣,“但后來想想,也能理解他們。”
而在武濤看來,在這一場博弈中,受影響的不只是非京籍孩子,“如果一個北京孩子認為,他上大學的競爭優勢來自于身邊外地戶口孩子的離開,這種心態對嗎?等到他踏入社會,面對不同價值觀、不同地域的競爭者,他又會用怎樣的心態去面對?”武濤擔心,雙方的爭論會演變成雙輸的局面,這對雙方孩子的成長都將產生不利影響。
遙遠的希望
2月29日,山東率先發布改革意見,從2014年起,凡在山東高中段有完整學習經歷的非戶籍考生均可在山東就地報名參加高考,與山東考生享受同等錄取政策。
這讓王莉隱隱地感到了一絲希望,“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改革還是會一步步推進的。”
2010年,北京義務教育放開對外地戶籍的限制也曾讓王莉感受到希望。本想在孩子升初中時就要回河北老家的她因此選擇了留京。
2010年5月,北京市教委發布政策表示,“只要是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非京籍子女,將保證其在京入學和接受教育”。各區縣教委公布2010年小升初政策,非京籍學生享受同城待遇,可享受派位、推優、特長生選拔等權利。
據悉,小升初政策的轉變緣于部分家長的努力與堅持。2009年,部分家長開始推動非京籍子女正常參加小升初,并于2010年3月,首赴海淀區教委表達訴求,此后每周一次到海淀區教委、北京市教委反映情況。
此后,申益、王莉、武濤、張猷等有相同訴求的家長聯合起來,不斷通過各種渠道發出取消中高考戶籍限制的呼吁。2010年2月起,北京家長率先自發成立“教育公平公民聯合行動”,隨后,上海、廣州、深圳等地的家長也加入到這一行動中。這些家長志愿者尋求支持者簽名,并將這些簽名連同訴求送到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呼吁盡快取消中高考戶籍限制,讓隨遷子女在經常居住地享有教育公平的權利。
2011年10月29日,隨遷子女家長發布民間版《隨遷子女輸入地高考方案》,建議各省區以學籍取代戶籍作為高考報名依據,允許非戶籍子女在經常居住地參加高考。
他們的呼吁也開始得到不少專家、學者的支持。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鐘秉林個人贊成異地高考,他認為,隨遷子女家長在一個城市工作生活,為這個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做出長期貢獻,跟隨他們在一起生活的子女,理所當然應該享受在這里受教育和參加考試的權利。但它在操作上確實有一定復雜性,他建議,異地高考實行后,北京、上海等地應更多地投放招生計劃指標,以保證不會影響到常住人口子女高考的利益。
雖然異地高考的改革之路還面臨重重困難,但申益說,即使兒子趕不上北京放開異地高考,他也還會繼續奔走呼吁,因為“每個孩子,不分戶籍、不分貧富、不分地位,都有獲得公平教育的權利。”
(應采訪者要求,文中家長均為化名)
對話
“高考戶籍限制違反《教育法》”
1
新京報:2009年11月,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曾向教育部提交《大學招生考試制度改革建議書》,這是你主持的研究課題的成果之一,其中是否涉及異地高考問題?是否收到教育部回復?
張千帆:當時還沒有注意到異地高考問題,直到2010年有些隨遷子女家長出來呼吁,這個問題才逐漸被人們重視。《建議書》主要關注大學對不同省市考生招生不公的問題,比如北大對北京考生就有所照顧。我們主張大學公平招生,北大和清華的招生標準可以不一樣,但他們都必須以同樣的標準面向全國考生。當時教育部也表示正在研究。那時正在制定國家教育發展綱要,但后來我們看到,綱要并沒有吸收《建議書》的主要主張。
2
新京報:為什么兩年后,你又和14位學者及社會人士向國務院遞交了聯合署名的《關于提請國務院審查并修改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規定>的建議》,呼吁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戶籍限制?之后是否得到國務院反饋?
張千帆:我那時的一個主要困惑是全國每年幾百萬考生遭歧視,卻沒有人站出來從法律上挑戰招生指標制度。直到后來隨遷子女家長出來呼吁,我們終于看到了改革招生考試制度的潛在推動力,于是再次就這個問題提出建議。
其實,高考戶籍限制違反了《教育法》,從法律角度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方式就是起訴,但教育部是國務院的下屬部門,所以我們通過行政復議程序提請國務院審查教育部的規定。事后我們得到了國務院的反饋,大家也看到目前教育部在著手解決這個問題。
3
新京報:你認為取消高考戶籍限制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張千帆:最大阻力在于地方的既得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尤其是京滬等教育發達省市的居民以及對決定招生和考試政策有影響的地方官員。畢竟開放戶籍限制將增加地方考生數量和競爭壓力,如果按照當地標準錄取還將占用各大學對當地分配的招生指標。目前,山東率先取消了戶籍限制,這是很好的,但山東畢竟不是矛盾最集中的地區,北上廣等地實現異地高考阻力會比較大。
其實,隨遷子女高考完全不涉及什么技術問題,它主要是全國高考試題不統一帶來的困擾。2002年后,我們開始實行“分省命題”,但時至今日,“分省命題”并沒有實現“提高素質教育”等當初承諾的好處,像北京學生高考的壓力依然很大。如果我們恢復2002年之前的統一高考,隨遷子女的高考問題也就解決了。
4
新京報:去年10月《建議》公布后,曾有很多人質疑它,你怎么看待這些反對聲音?
張千帆:北京等地考生和家長有一些反對聲音,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放開戶籍限制會增加本地考生的競爭壓力。有些教育學者可能也對實行全國統一高考等建議存有質疑,認為是搞“大一統”,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可以說,總的改革方向是沒什么人反對的,只是在一些具體改革措施上有些人存有異議。
5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隨遷子女家長們共同起草的《隨遷子女輸入地高考方案》?
張千帆:我認為家長們的訴求是比較合理的,提出要求也是憲法賦予的權利,而且方案也確實考慮了當地困難。從方案具體內容來看,我認為一些措施如“北京、上海兩地,隨父母在經常居住地上學,至高中畢業有連續4年以上學籍的,高中畢業即可在經常居住地參加高考和錄取”等,也能比較有效地解決目前的問題。
但我們也可能采取更加保守的方案,對各項標準制定得更嚴格,這需要地方政府部門權衡各方利益,確實存在一定難度。
6
新京報:《建議》以解決異地高考問題入手,最后提出實現全國統一高考及實行公平的大學招生與考試制度,請問這些建議的原因和具體解決方式是什么?
張千帆:解決國內大學的招生與考試制度問題肯定是要分階段進行的,目前異地高考問題迫在眉睫,需要首先解決。這個問題解決后,其他問題會接踵而來。我認為恢復統一高考是必須的,它是大學公平招生的必要條件。但統一高考并不是充分條件,我們還需要在統一高考的基礎上再根據大學的特色和要求進行自主招生。目前國內自主招生是高考前進行,主要是給考生高考加分,這其實是違背自主招生初衷的。而且現在大部分考生是沒有機會參加自主招生的,這也不公平。我們需要改變自主招生的性質,能在統一高考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的自主招生,并且能夠在原則上公平錄取,這是我所期望的。
更多內容,請查看 北京招生網 專題
更多招生簡章,請查看“高考資訊”頻道
更多高校,請查看“院校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