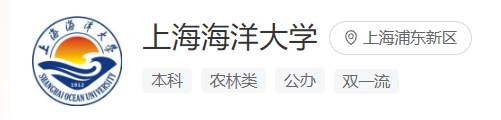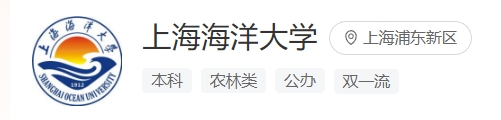金賢姬,作為朝鮮勞動黨的“工作員”的名字是“金玉花”、“金花玉”,1964年1月生于平壤,生就一副美人坯子。其父是朝鮮外交部官員,曾作為外交官攜眷常駐古巴,妹妹賢玉和弟弟賢洙就出生在哈瓦那。金賢姬上小學時,就曾作為童星演過電影;中學時代,曾作為青少年代表向出席南北和談的南方代表獻過“金達萊”;曾就讀于金日成綜合大學(生物)和平壤外國語大學(日本語);1980年3月,被朝鮮勞動黨“調查部”選中,遠離家庭,在若干“特殊機構”里長年接受包括外國語能力在內的旨在培養一流“工作員”的各種訓練,可以熟練使用日語和中文(包括廣東話)。 在接到回國的密令火速趕回平壤之前,遵照“本部”的指示,她正為了爭取澳門政府以中國大陸偷渡者為對象的“特赦”名額(目的是“合法”獲取澳門公民的身份證)而第二次潛入中國廣州,進行“澳門滲透工作”的準備。當時,她化名“吳英”,為了應對葡澳移民當局的盤查,事先編好了一個籍貫為黑龍江省“五常市”的中國女孩,在“文革”中父親受迫害自殺,母親被迫改嫁,幼小的“吳英”被寄養在鄰家,從小飽受流離之苦的催人淚下、天衣無縫的故事。而在此之前,從1985年7月到1987年1月,她和另一名名叫“金淑姬”的工作員一起,持偽造的日本護照在廣州和澳門進行過長達一年半的“語學實習”(目的是學習中文、粵語,為“滲透澳門”做準備)。
有一個細節值得一提。1987年10月末,正在廣州的金賢姬接到“火速回國”的密令后,立即途經北京回平壤。在北京短暫逗留中,作為“黨的女兒”、同時也是父母的“乖乖女”的金賢姬不忘給母親買了樣式新潮的毛背心和牛黃清心丸、鹿胎膏等中成藥。但這些都成了徒勞。一回到平壤,金賢姬就接受了最高當局的“讓大韓航空的飛機消失”的密令,參加了屬于國家最高機密的“工作組”,當然不可能自由行動。在后來發表的手記中,她對“行動”前未能與親人告別,并把從北京買的禮物親手送給媽媽而深感痛楚。
從1981年7月初到1983年3月中旬,在一個稱為“特閣3號招待所”的保密機關里,金賢姬度過了20個月與世隔絕的生活。在這里,她與一個叫“李恩惠”的日本女性“同吃同住”、接受了徹底的日本人化教育。除了在1982年3月至4月間,因“入黨”而有過幾天短暫的公出外,20個月,“每天24小時都是與恩惠老師一起度過的”。在“開學”伊始,代表“上級”組織的“李指導員”對她和李恩惠的約法三章是:1.按照課程表嚴格實施教學;2.從即刻起,恩惠老師和玉花(金賢姬)全的會話只能用日語,嚴禁用朝語;3.玉花跟恩惠老師不僅要學習日語,還要學習日本人的舉止、風習、化妝方法乃至思考問題的方式等,直至可達到亂真的程度。
正是根據金賢姬提供的關于“李恩惠老師”的細節,日本方面判斷出“李恩惠老師”的真實姓名與身份是被綁架的日本女性田口八重子。
1983年3月中旬,玉花接到“李指導員”的“今天結束學習,馬上轉移到別的招待所,立即打點行李出發”的命令后,與李恩惠告別的情景令人感動:“她向我行禮道謝,把自己珍愛的金筆送給了我。我回贈她一塊可兼用作包袱皮的圍巾……告別的時候到了,恩惠老師站在招待所的門前,手里揮動著我給她的圍巾,直到我乘坐的奔馳車從視線中消失。”
后來又經過長期的準備,“偽裝日本人工作”正式啟動。1984年8月至10月,金賢姬與搭檔金勝一以“日本人父女”的面目甚至進行了一場實地彩排。他們從平壤出發、經莫斯科、東柏林、布達佩斯等城市到了維也納和巴黎,最后經北京回到平壤。在社會主義“同盟國家”,他們使用朝鮮外交部發行的公務護照;而在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第一次使用了偽造的、分別署名“蜂谷真由美”和“蜂谷真一”的“日本護照”。
1987年11月12日,“蜂谷父女”在一紙致黨中央、宣誓“為了粉碎國際反動勢力策動兩個朝鮮的陰謀,為了共和國的統一,我們將……”的《誓約書》上莊嚴地摁上手印之后,從平壤順安機場出發了。他們途徑莫斯科飛往東柏林,而后又輾轉維也納、羅馬、布拉格等城市,從貝爾格萊德抵達巴格達,終于按既定計劃從巴格達登上了作為此行目標的“大韓航空KAL858”航班。在登機20分鐘之前的當地時間22點40分,“蜂谷真一”裝作聽收音機,將那臺乍看跟日本造“Panasonic”半導體一模一樣的定時炸彈取出來,從容地將定時器的指針撥到9個小時以后,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將“半導體”裝回到塑料袋里。“真由美”在一旁看著他“操作收音機的手指的動作,有一種連呼吸都要停止了的緊迫感。”此時的金賢姬,似乎還沒有意識到她已經踏上了一條不歸之路。9小時后,KAL858航班在印度洋上空爆炸,115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罹難。
1990年3月27日,金賢姬被漢城地方法院判處死刑。后蒙盧泰愚總統“特赦”,于一年后被釋放。后在安企部的保護下從事著述和講演。其后來出版的題為《現在,作為女人》的手記,在韓日兩國都成為暢銷書,后又被拍成電影,據說僅版稅一項就高達10億韓元。1997年12月,與當時曾參與她的調查工作的原安企部官員秘密結婚,現在韓國過著“普通主婦”的生活。
有一個細節值得一提。1987年10月末,正在廣州的金賢姬接到“火速回國”的密令后,立即途經北京回平壤。在北京短暫逗留中,作為“黨的女兒”、同時也是父母的“乖乖女”的金賢姬不忘給母親買了樣式新潮的毛背心和牛黃清心丸、鹿胎膏等中成藥。但這些都成了徒勞。一回到平壤,金賢姬就接受了最高當局的“讓大韓航空的飛機消失”的密令,參加了屬于國家最高機密的“工作組”,當然不可能自由行動。在后來發表的手記中,她對“行動”前未能與親人告別,并把從北京買的禮物親手送給媽媽而深感痛楚。
從1981年7月初到1983年3月中旬,在一個稱為“特閣3號招待所”的保密機關里,金賢姬度過了20個月與世隔絕的生活。在這里,她與一個叫“李恩惠”的日本女性“同吃同住”、接受了徹底的日本人化教育。除了在1982年3月至4月間,因“入黨”而有過幾天短暫的公出外,20個月,“每天24小時都是與恩惠老師一起度過的”。在“開學”伊始,代表“上級”組織的“李指導員”對她和李恩惠的約法三章是:1.按照課程表嚴格實施教學;2.從即刻起,恩惠老師和玉花(金賢姬)全的會話只能用日語,嚴禁用朝語;3.玉花跟恩惠老師不僅要學習日語,還要學習日本人的舉止、風習、化妝方法乃至思考問題的方式等,直至可達到亂真的程度。
正是根據金賢姬提供的關于“李恩惠老師”的細節,日本方面判斷出“李恩惠老師”的真實姓名與身份是被綁架的日本女性田口八重子。
1983年3月中旬,玉花接到“李指導員”的“今天結束學習,馬上轉移到別的招待所,立即打點行李出發”的命令后,與李恩惠告別的情景令人感動:“她向我行禮道謝,把自己珍愛的金筆送給了我。我回贈她一塊可兼用作包袱皮的圍巾……告別的時候到了,恩惠老師站在招待所的門前,手里揮動著我給她的圍巾,直到我乘坐的奔馳車從視線中消失。”
后來又經過長期的準備,“偽裝日本人工作”正式啟動。1984年8月至10月,金賢姬與搭檔金勝一以“日本人父女”的面目甚至進行了一場實地彩排。他們從平壤出發、經莫斯科、東柏林、布達佩斯等城市到了維也納和巴黎,最后經北京回到平壤。在社會主義“同盟國家”,他們使用朝鮮外交部發行的公務護照;而在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第一次使用了偽造的、分別署名“蜂谷真由美”和“蜂谷真一”的“日本護照”。
1987年11月12日,“蜂谷父女”在一紙致黨中央、宣誓“為了粉碎國際反動勢力策動兩個朝鮮的陰謀,為了共和國的統一,我們將……”的《誓約書》上莊嚴地摁上手印之后,從平壤順安機場出發了。他們途徑莫斯科飛往東柏林,而后又輾轉維也納、羅馬、布拉格等城市,從貝爾格萊德抵達巴格達,終于按既定計劃從巴格達登上了作為此行目標的“大韓航空KAL858”航班。在登機20分鐘之前的當地時間22點40分,“蜂谷真一”裝作聽收音機,將那臺乍看跟日本造“Panasonic”半導體一模一樣的定時炸彈取出來,從容地將定時器的指針撥到9個小時以后,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將“半導體”裝回到塑料袋里。“真由美”在一旁看著他“操作收音機的手指的動作,有一種連呼吸都要停止了的緊迫感。”此時的金賢姬,似乎還沒有意識到她已經踏上了一條不歸之路。9小時后,KAL858航班在印度洋上空爆炸,115名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罹難。
1990年3月27日,金賢姬被漢城地方法院判處死刑。后蒙盧泰愚總統“特赦”,于一年后被釋放。后在安企部的保護下從事著述和講演。其后來出版的題為《現在,作為女人》的手記,在韓日兩國都成為暢銷書,后又被拍成電影,據說僅版稅一項就高達10億韓元。1997年12月,與當時曾參與她的調查工作的原安企部官員秘密結婚,現在韓國過著“普通主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