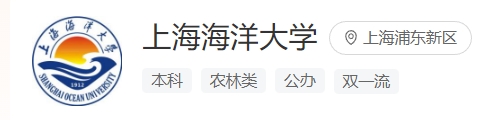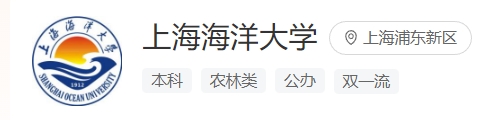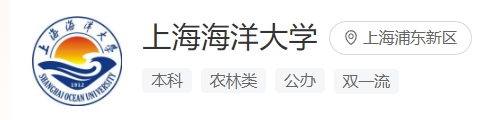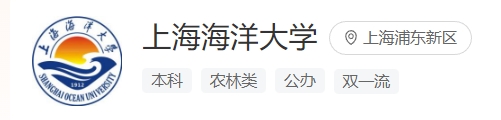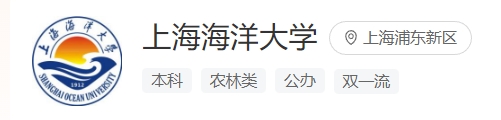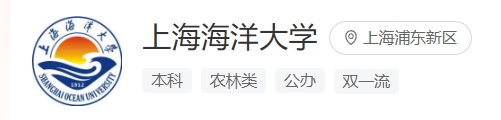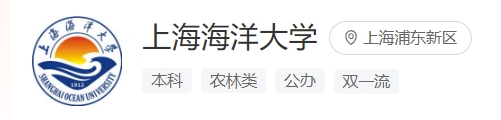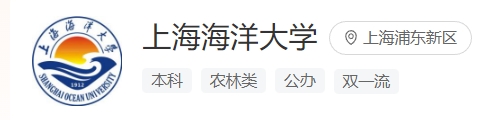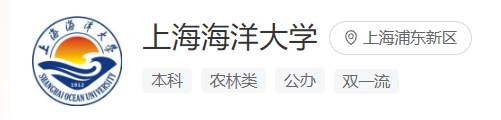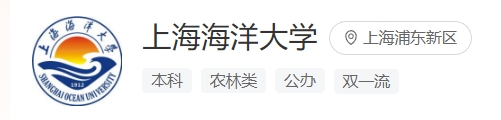同一種記憶
家庭成員經常聚在一起,時不時回清華園走走看看。“我和我媽就常說起宿舍,巧了,我們住的是同一棟樓,我住一樓,她住在二樓。”
同一個氛圍
父母都是清華出來的,這又是一種“潛移默化”。聶昕就說,自打有高考想法開始,就沒想過考其他學校。
同一份感情
對于母校,聶家人無一例外都談到了清華嚴謹的學風和進取的精神,他們感謝清華的教育和培養;六位老清華中三位是校體育代表隊員,這一點可以說是清華的“校傳”。
24日,是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成都商報記者近日發現,有這樣一個家庭,40多年間,兩代人共有13名成員走出清華園,占到清華畢業生總數近萬分之一———清華大學100年,培養了17萬名學生。
這個家庭的成員現在北京、美國安靜地生活著,聽說過他們的人都驚嘆不已,而他們卻自認平凡。
唯一沒考上清華的 是哈佛博士后
舅舅聶光啟說:“她是學醫的,如果要考清華,一定考得上!”
1957年,聶家的大姐聶皎如考入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兩年后,二弟聶光啟考入清華大學電機系,又過了一年,小妹聶皓如也考進電機系。
聶皎如姊妹三人共有六個孩子,其中五個進入清華的孩子在家庭里被稱為“小清華”。
唯一沒上清華的是聶皎如的女兒唐炬,舅舅聶光啟說:“她是學醫的,如果要考清華,一定考得上!”
唐炬1985年考入北京醫科大學,獲博士學位,曾在哈佛醫學院做博士后,現在美國當醫生。
繞了半個地球,還是“清華”牽線
“我和我媽就常說起宿舍,巧了,我們住的是同一棟樓。”
這個清華家庭還在不斷擴大,三位老清華都在校園里找到了另一半。聶皎如和丈夫唐慶祥,還有來自青島的李有潤是同班同學,聶家在北京,李有潤常去玩,因此認識了聶家小妹聶皓如。二弟聶光啟曾是校運會跳高冠軍,與女隊跳高能手、電機系的師妹黃群芳結成了情侶。
和父母不同,聶昕和丈夫連錚在清華時并不認識,一個是88級電機系,一個是85級建筑系,直到兩人畢業后,同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留學時才開始交往。
繞了半個地球,還是“清華”牽線,有緣人終于結成良緣。
小清華中,老大李錚的太太叫李小霞,李小霞本科不是在清華讀的,后來拿到了清華大學計算機系的碩士學位。
至此,聶家13位清華學子到齊,家庭成員感情極好,經常聚在一起,時不時回清華園走走看看,那是記錄了他們青春歲月的地方,雖然相隔幾十年,卻有相同的回憶。聶昕和父母都出自電機系,“我和我媽就常說起宿舍,巧了,我們住的是同一棟樓,我住一樓,她住在二樓。”
祖母給六個孫輩每人一本相冊
“我姥姥評價一個人,不是看世俗的東西,她看這個人是否快樂……這個要求挺高的。”
三位老清華的母親叫齊祖評,“是個睿智的老人。”兒孫都這樣評價她。
聶光啟回憶,他的父親聶國忱和母親齊祖評都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學畢業生,姑姑聶毓禪是位杰出的女性,是中國現代護理教育奠基人。
“抗日戰爭時期,1943年初,我父親和她一起從北京輾轉去四川共赴國難,途中不幸身亡,當時皓如才兩個多月(央視十套制作的紀錄片《烽火天使》記述了這段經歷)。從此母親帶著三個孩子含辛茹苦,但她從來沒有放棄對三個兒女的教育。她很有眼界,告訴三個兒女,你們念書能念到哪,我就供你們到哪,直到你們長大成人,她的三個子女以及孫輩們陸續考入清華大學和她的培養和教誨是分不開的。”
齊祖評給六個孫輩每人一本相冊,相冊的扉頁上都是她寫給孫輩的話,根據每個孫子的性格,寫的話也完全不同。
在聶皓如二兒子李嘉的相冊里,齊祖評工整地寫道:人不僅靠肢體站立,更要靠思想站立,人不僅靠食物生活,更要靠理想生活。老人家當然知道現實的殘酷,給李嘉的第二段話是這樣的:同在一個環境中生活,強者與弱者的分界,就在于誰能改變它。
雖然重視教育,但齊祖評認為,除了學業,身體健康、生活快樂也很重要,外孫李錚初中沒考上重點,父母都挺急的,但她覺得沒啥。“我姥姥評價一個人,不是看世俗的東西,她看這個人是否快樂,自己快樂和給周圍的人帶來快樂,這個要求挺高的,不是考試分高、能掙錢、能當官就能達到的。”很多年以后,李錚回憶起來,認為姥姥固然教了他們一些知識,認認字,簡單的算術,背名人名言什么的,但最重要的是對子孫品格的影響,她為這個大家庭創造了溫暖、公平、開明、追求上進但又不功利的氛圍,“姥姥很特別,世事洞明,但你讓我說她有什么教育理念,我也說不出來,她的行為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
齊祖評2005年去世,享年93歲,電話里和成都商報記者說起奶奶,聶昕仍然一度哽咽,傷心得說不下去。李有潤本人就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對于教書育人有豐富的經驗,他說,他想寫篇文章,講述岳母的教育方式,以作紀念。
家里的話
●“像我弟弟,都沒見過他開夜車做作業”
●幾個小清華,小時候聚在一起也是玩,打撲克,從不交流學習
●身教重于言教;學習的壓力不能從家長那來
●父親李有潤把課本看一遍,然后畫張表,列出知識結構,點撥一二就行了
●聶家人無一例外地反對“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學業太重,報各種班”等等
家傳
怎樣才能上清華?
怎樣能上清華?無數人都會問。聶家人的回答很簡單,那就是認真,上進再加上一顆平常心。
聶家人普遍學習輕松。聶皓如讀書那會,一周學習五天半,最盼望一天半的周末休息,可以好好玩,幾個小清華,小時候聚在一起也是玩,打撲克,從不交流學習。
李錚分析原因,一是遺傳,“我們家人腦子都不笨,都挺會考試的。我還算比較刻苦的,像我弟弟,公認的家庭里相當聰明的,我都沒見過他開夜車做作業。他還給我說:只要有標準答案的題目,我一看就知道老師想要什么答案!”
還有就是家庭的氛圍,父母都是清華出來的,這又是一種“潛移默化”。
1987年,李錚成為小清華中的第一人,他能感覺到,后面的弟弟妹妹都把清華當成目標,聶昕就說,自打有高考想法開始,就沒想過考其他學校。
清華大學的理工科,是中國優秀人才集中的地方,聶家每個人似乎都長著一顆理工科腦袋。
“我就喜歡理工科,數學啊,物理啊,特有意思。”聶皓如承認,上清華有哥哥姐姐的影響,也和自己的愛好有關系。
清華女生,尤其是理工科女生,一直很稀缺,不過也有聶昕這樣的女生,以當年電機系北京考生第一名的成績進入清華,讓須眉汗顏。
進清華后,她所在的班30人,女生只有五個,聶昕自己倒沒覺得有什么特別的:“這得看人,不看性別,喜歡理工科就好,我們家的人都比較理性,讓我學文科的話,反而摸不著頭腦。”
家教
反對“越嚴厲越出息”
一個虎媽,讓東西方的教育理念發生碰撞。難道真的是父母越嚴厲子女就越有出息?聶家每個人都對此說NO,當孩子時,他們學習輕松,為人父母后,他們也給了子女寬容和信任。身教重于言教,不止一個聶家人這樣說。
六位老清華畢業后,聶皎如夫婦進了林業部林產工業設計院,聶光啟夫婦去了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聶皓如在首鋼工作,李有潤在清華當老師,都是各自單位的技術骨干,工作很忙,“所以我們都沒有太多時間管子女的學習。”
照李錚看來,現在好多家長教育不得法,天天盯著孩子學習,“這沒用,得孩子自己體會。”他上高中時,父親李有潤會把他的課本看一遍,然后指導他畫一張大表,列出知識結構,點撥一二就行了。
平時做父母的基本不會批評兒子,某次大考前,李錚還在認真地看電視,李有潤想了半天,才忍不住“提醒”兒子明天要考試,李錚一聽,相當不高興,撅著嘴走了。 “他小學成績不好,但上中學后自己知道努力,自學能力蠻強的。”在父母的引導下,李錚高中考上了清華附中重點班。
聶昕、連錚夫婦有兩個孩子,女兒三年級,兒子一年級。根據自己的學習經驗,聶昕認為好的教育方法是讓孩子覺得學習是自己的事,“學習的壓力不能從家長那來,這是個惡性循環。他們總會獨立,如果哪一天沒人管了,又該怎么辦呢?他們自己明白怎么做,家長也省心。”
聶家人無一例外地反對現在的某些教育方式: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學業太重,報各種班等等,“希望孩子有好習慣,有健康的心態,對自己有要求,沒必要給他們設立什么目標。”
家風
“清華家庭”的淡定
清華、北大,幾乎是中國人的高校夢想。父母教育孩子,會說:“長大了上清華北大!”老師熟人夸獎:“這孩子能上清華北大!”小孩自己立志:“我要上清華北大!”更有甚者,記者有位女性朋友,發誓非清華北大畢業生不嫁!這兩所名校,就是標桿,就是境界。普通人家,要是高考出了個清華或北大的學生,那肯定是全家歡喜,大放鞭炮,大宴賓客。再多出幾個,就是奇跡了,至于兩位數,想都不敢想。
而身在“清華家庭”,其中的人卻非常淡定,覺得自己沒有什么了不起。大姐聶皎如說,他們都是很普通的人,畢業后認真工作幾十年,然后退休,沒什么可說的。聶昕認為,大家從小就在一起,感覺沒什么稀奇,她的同學中也有一家四口上清華的。倒是聶家的女婿比較上心,李有潤幾年前給清華校友通訊寫了一篇文章,講述聶家的清華情,他覺得這段珍貴的家史應該記錄下來。
對于母校,聶家人無一例外都談到了清華嚴謹的學風和進取的精神,他們感謝清華的教育和培養,懷念在清華的歲月,聶家全家喜愛文體活動,六位老清華中三位是校體育代表隊員,這一點可以說是清華的“校傳”。
采訪的最后,聶家人深情地說出心聲:“清華歷史已屆百年,我家‘老清華’就讀于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小清華’就讀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正是我國教育蓬勃發展的兩個好時期,我們趕上了。國順則家順,清華大學哺育了我家兩代人,我們對清華懷有無法割舍的情懷。在國家各個行業,各個領域,各個角落都有清華學子的身影和足跡,他們努力著,奮斗著,奉獻著,我們,有幸成為這個群體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