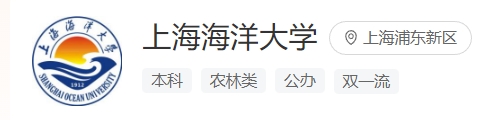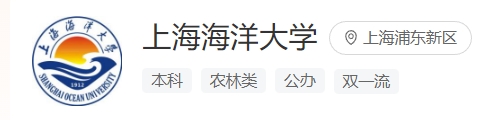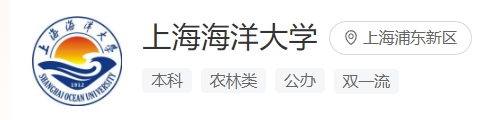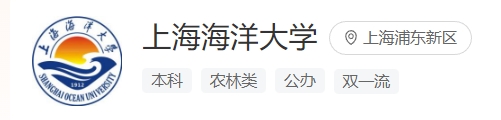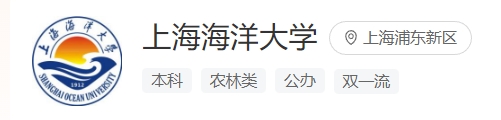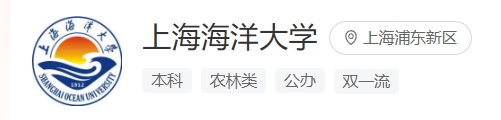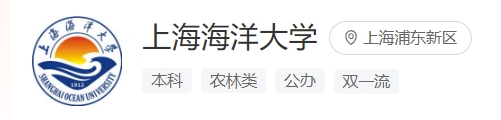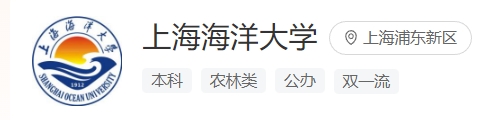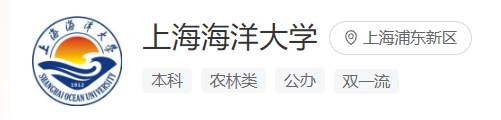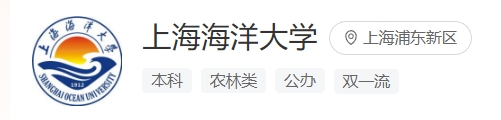“某市今年高考總分750分,高職錄取線150分,較2010年下降140分,缺口仍然很大。”近日,高考招生工作剛結束,一所三本高校分管招生的副校長王平(化名)就忍不住向中國青年報記者抱怨:“三批次錄取的高校(即獨立學院——記者注)已經感受到了陣陣寒意。”
王平回憶,2008年和2009年,他們學校第一志愿的錄取率還是100%;從2010年開始情況逆轉,當年錄取率下降為80%;2011年更是猛然降至50%,最后是通過不少“技術處理手段”才勉強完成招生計劃。
“這種下降趨勢不知何年是盡頭?”王平說,全國高校生源危機中,323所三本高校首當其沖,他們不僅要應對第一志愿錄取率直線下降的局面,還要面臨專業穩定率不高,學生學習動力先天不足等考驗。
于是,請分管教育的副省長吃飯保住生源,到教育部門退掉剩余的招生計劃,舉辦周六補習班與本科預科班……為應對危機,各三本高校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清華、北大都難“掐尖”了,三本墊底更失落
2008年,全國高考人數達到1050萬的頂峰,隨后開始下降。2011年,下降至933萬,比2010年減少24萬左右,資料顯示這種下降趨勢將持續至2018年。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教授姚遠說,導致高考人數下降的直接原因是我國人口出生高峰期已過,人口自然增長率降低。
以人口出生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北京市為例,2006年高考考生11.3萬人,2011年下降至7.65萬人,2013年大概6萬人,其中還有約20%的考生會棄考出國留學,實際參加高考人數將只有5萬多人。
“在這場高考生源危機中,清華、北大等一本老大哥都難‘掐尖’了,三本墊底的高校更失落。只有既不靠前、又不墊底的二本高校最不敏感。”北京一所三本高校的校長盧開(化名)說,2011年全國高考中有40名省、市狀元向香港大學 (微博) 遞交申請,最后港大錄取了17名省、市狀元,較2010年增長一倍。北京40名可上清華、北大的高分考生被香港大學錄取。此外,被譽為“美國高考”的SAT尚未在中國內地開考,不過2011年內地赴香港參加SAT考試的學生達6000多人次。“看到這些情況,清華、北大的校長不著急嗎?”
二本高校因為15%的高分考生輪不到其錄取,另15%墊底的考生想進又進不去,他們一直錄取中間分數段高考考生,受到的沖擊最小。
“三本高校招不到生就將自斷財路,破產倒閉。”王平說,很多三本高校在學校所在地招不滿高考考生,就紛紛到河南、河北、山東、安徽等生源大省去跑馬圈地搶生源,甚至把在A省落空的招生指標通過技術處理,調劑到B省進行錄取。
過去,三本高校在招生宣傳時恨不得把錄取分數線“吹”得老高,以凸顯學校的品牌影響力與教育質量之好,吸引更多高分考生來報考。現在,高考生源市場競爭激烈,三本高校就得想方設法把錄取分數線說得越低越好,以免低分考生怕錄取不了不敢填報志愿,高分考生又不屑于報考,結果兩頭落空。
僧多粥少,副省長只能先保省內高校“吃飽”
三本高校發展的處境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王平說,1999年高校大擴招,政府給高校下達招生任務,這所高校增加300個招生計劃,那所高校追加500個錄取指標,要求大家共同努力把大學擴招的目標完成好。三本高校趁勢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
當時,三本高校到教育部門爭取招生指標幾乎擠破腦袋。因為拿到招生指標就意味著開通了財路:公辦高校的財政撥款是按學生人頭數下撥的;三本高校多招收一個學生就可以多收一筆學費。同樣一個500畝的校園,招生越多高校的辦學成本就攤得越薄。
王平透露,以往每年春節前,他都要參加生源大省分管教育的副省長宴請北京80多所高校校長的活動。這些分管副省長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希望第二年這些學校在給該省下達招生指標時每校多增加幾人。“幾乎都能如愿以償。”他說。
當河南省高考考生從2009年的96.5萬下降到2011年的85.54萬時,已經變成校長請副省長吃飯了,但這個請飯難度就大多了。“僧多粥少,人家副省長要優先確保省內高校‘吃飽’,也顧不上省外三本高校。”王平說。
“一切都是圍繞生源而變。”針對三本高校的各種招生策略,一位地方的招生工作人員一語點出了要害,“要什么樣的政策都好說,關鍵是有沒有考生填報你們學校。”
今年,全國只有四個省的高考生源沒有出現下降,甘肅省是其中之一。北京某三本高校原計劃到甘肅多招收一些學生,分管招生工作的副校長去了兩趟,結果報名數不及錄取計劃的80%。不要說按150%、120%的比例進行投檔,就連一比一的錄取投檔目標都實現不了,因為沒有學生報考。
無奈之下,部分三本高校分管招生的校領導與招生辦主任開始把剩余的招生指標退還給教育行政部門。
這里面還有學校的一些“小算盤”。
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門對三本高校的評估都是以招生指標為準繩。現在不少三本高校辦學資源本身就不夠,招錄的學生越多,離評估達標的標準越遠。通不過評估的三本高校將被停止招生甚至摘牌。對學校來說,能否多招生、少招生待通過評估以后再說,眼前重點要解決有沒有招生資格的問題。
另一方面,三本高校對分管招生工作的校領導與具體的工作部門都有量化的考核,即招生任務完成率等。退掉一部分招生指標,完成任務至少可以先把獎勵拿到手,至于明年的招生形勢與規模,以及學校的可持續發展,實在是無暇顧及。
“世紀寶寶”拯救不了三本高校
王平說,非常羨慕那些民辦教育培訓機構,他們在市場打拼,雖然很辛苦但終究生存了下來,且生命力越來越強。不像他們這些三本高校,至今躺在招生計劃的“溫床”上,競爭力也在慢慢喪失。假如像部分高職一樣實行注冊入學,有學生報考的話就給指標,否則就不給指標,三本高校將有多大的生存空間與能力。
“當前一本、三本高校生源危機的實質就是對中國高等教育不信任。”王平說,三本高校學生學習四年需要10多萬元,但可能畢業后10年都收不回這筆投資。這種“高收費、低含金量”的發展模式正在受到空前挑戰。
同時,三本高校自身是否過硬也一直是社會公眾詬病的焦點。部分三本高校的投資方只顧收取學費,獲取眼前利益,招錄一些高考分數只有100多分至200多分的學生進來與本科生一同接受教育,這令一些三本院校的老師很頭疼,“基礎太差,沒辦法教。”一些學校不得已,只好給這部分學生補基礎課的“短板”,在周六辦起補習班與本科預科班。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民辦教育是我國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一年多來并沒有出臺相應的配套政策。一位三本院校校長說:“三本高校發展整體進入‘寒冬’是不爭的事實。一批軟硬件不好,還處于投資階段,以及把學費挪用到其他領域的三本高校都有可能被市場所淘汰。”
部分三本高校把復蘇的希望寄托在“世紀寶寶”身上,即2000年出生的孩子在2018年參加高考時,生源總量開始止跌并走向平穩。可王平對此并不樂觀,“世紀寶寶拯救不了三本高校。”在他看來,三本高校突破高校生源危機,需要同時做好加法與減法工作,即加大投入,提高辦學內涵與質量;降低學費收費標準,讓更多的考生進得來,學得起,有東西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