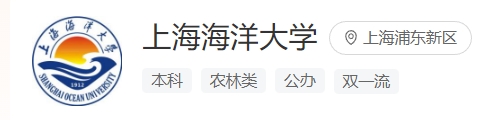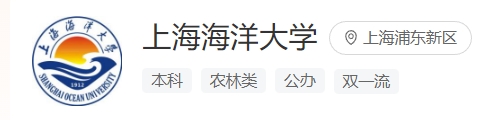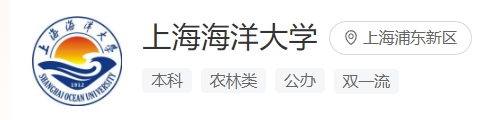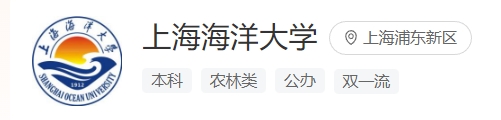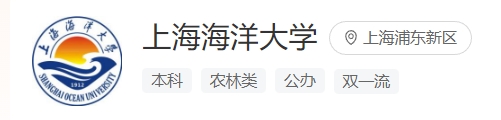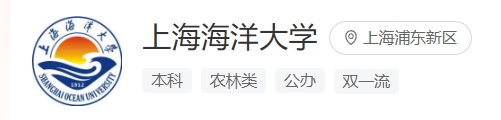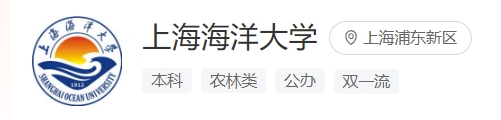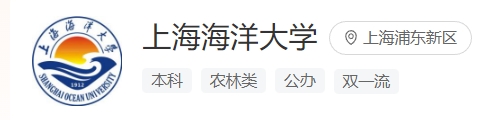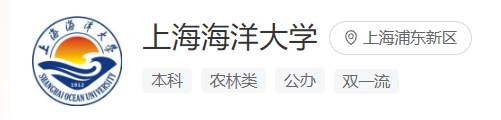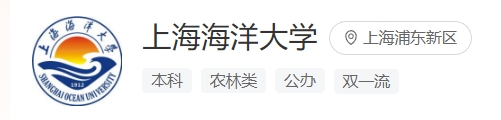又一個新學年開始了。近日,廣州有媒體對廣州外來工子弟學校進行調查時,聽到辦學者這樣一段最辛酸的描述:不管哪一層次流動人口子弟學校,校園里清一色的“外”和清一色的“低”——外來工管理、外來工執教、外來工子女就讀;低投入的學校,低工資的教師,低收入的農民工子女。
外來工子女不是私生子,這是常識;外來工子弟學校,也不應該是國民教育體系的“私生子”。然而,無論是外來工子弟學校,還是在這些學校就讀的外來工子女,他們的身份都沒有享受到應有的“國民待遇”。
華南師范大學基礎教育培訓與研究院副院長王紅,帶領學生用4年時間調查形成了《廣州市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研究報告》,該報告顯示:截至去年底,廣州有51萬農民工子女在穗接受義務教育,但六成在民辦學校就讀,廣州既無法真正做到義務教育“以公辦為主”,又對民辦學校財政資助嚴重不足。
正因為這種“嚴重不足”(當然還有其它原因,例如年審、稅收、用地、融資、教師隊伍建設等政策上的歧視),造成了外來工子弟學校始終在低水平上徘徊,有的還面臨關停、倒閉的危機。
城市化的進程決定了外來工及其隨遷子女的隊伍不斷擴大。在流動人口大量涌入的廣州,這一社會現象尤為突出。客觀地說,為了填補政府基本公共服務的不足,從1994年出現第一所外來工子弟學校至今,目前廣州的這類學校已經有約200所。有教育界人士指出:這些學校幫了政府,幫了社會的大忙。但在許多外來工子女流入地,當地政府部門只是對外來工子弟學校進行“監管”和“規范”,甚至任其自生自滅,根本上談不上扶持和服務。
廣州雖然從2008年起設立了民辦教育發展專項資金,每年約1000萬。但區區1000萬,對眾多民辦學校,無疑是僧多粥少。據調查,辦得好的學校可獲15萬元,有些學校可獲幾萬元,很多的學校則根本沒機會獲得資助。此外,由于這筆專項資金是用于改善教學設備的專款,所以基本上起不到減輕外來工子女就學負擔的作用。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如何解決好外來工子女就學的問題,根本出路是在中央財政的支持下,建立起以流入地政府為主、以公辦學校為主的外來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保障機制。與此同時,政府應加大對外來工子弟學校的扶持力度,通過購買學位等方式,對其進行經費補貼。
外來工子弟學校及其就讀的外來工子女能否擺脫“私生子”待遇,能否公平獲得教育資源,不僅影響“新廣州人”家庭的前途,更關系到未來“新廣州人”的素質。我以為,外來工子女教育,不僅是外來工的家事,也是政府的政事。
提供義務教育本來就是政府應當承擔的責任,不能再推給社會,推向市場了。